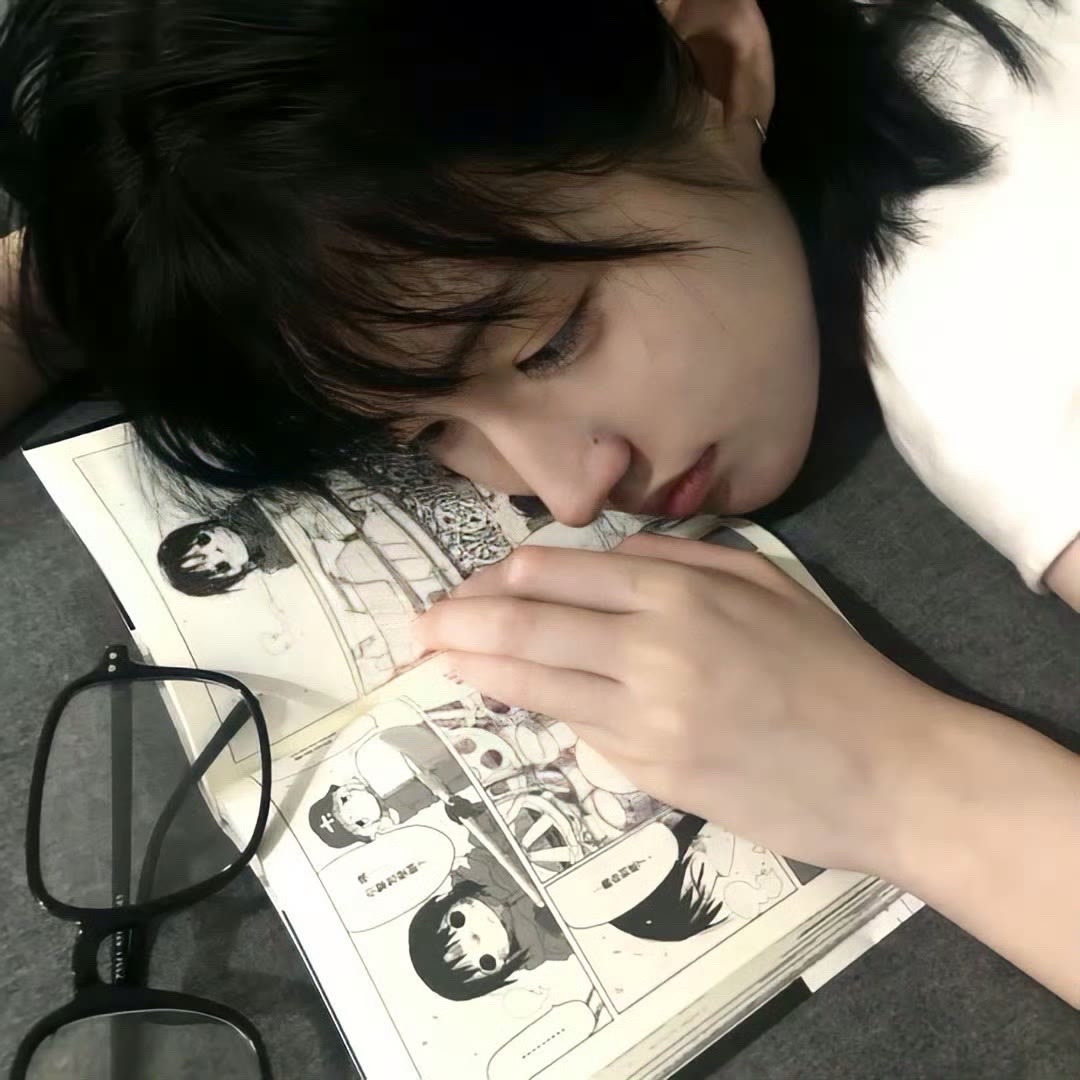
小說
白純從父親的手里掙脫出右手,然后對龜茲眾將說道:你們護送陛下回屈茨城。身甲又分胸甲、背甲、肩片、脅片。胸甲和背甲采用了北府獨創(chuàng)地板甲,在板甲周圍圍滿了鐵山文甲;肩片和脅片采用了小片地鐵魚鱗甲。身甲里面還網了一層連環(huán)甲,最里面襯了一層棉布,防止磨傷身體。而甲裙、甲袖是夾鐵夾皮的柳葉甲,頸、肩、肘、膝等關節(jié)處則是采用了鐵圈甲,保證整個甲衣的靈活性,再配上圓盤鐵頭盔、面罩和戰(zhàn)靴,簡直就是一個移動地鋼鐵戰(zhàn)士。
于闐國忙于應付先零勃的羌騎兵,就是想支援龜茲國也有心無力,而疏勒國在諸國的最西邊,暫時還沒有機會和北府直接對抗,所以就在那里磨洋工,答應好的三萬兵馬兩、三個月了都還沒有過尉頭。龜茲國只好獨立支撐起東線戰(zhàn)場,這讓相則很是感嘆,人心散了,隊伍不好帶了。華不會嫌手下兵馬太多,關鍵是這些兵馬必須是精銳聽從自己的命令。不過這幾部大人各自隆重推薦地兵馬也不會太差,要不然就丟面子了。而且經過這段時間的草原大換血。各部部眾對這位鎮(zhèn)北大將軍是敬畏如神。也已經知道按照這位大將軍的軍法。要是在戰(zhàn)場上怯戰(zhàn)退卻是違了軍法,不但自己會被砍掉腦袋,就是同隊的同伴、家里的親人都要受到牽連,按照這位大將軍森嚴的軍法算下來恐怕會砍掉一大片腦袋,沒有誰不怕!
國產
- 中文教育在校園中的重要作用與發(fā)展趨勢
- 關于99二區(qū)的科學研究與發(fā)展現狀分析
- 午夜時分的科學奧秘:時間、心理與生理的深度解析
- 小說作為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及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分析
- 影院中的日韓影片:文化差異與審美趨勢解析







一區(qū)(4)
天美
說到這里,冉閔轉過頭去望向南皮城,像是自言自語道:魏昌一戰(zhàn),不但是我,恐怕慕容恪等燕國上下也已經膽喪。不知道當我有膽對陣北府軍的時候,還會不會像今天這般氣盛?極限戰(zhàn)一時延續(xù)到十月底漠北大雪紛飛的時候,曾華屬下各部終于收手了,打著飽嗝清點著搶來的戰(zhàn)利品,然后準備安安心心過冬了。
曾華的腳步也放得極輕,一步一步地走在正道上,他的身也和正道一起時不時地隱現在樹蔭和黎明的幽暗之下。走過一段不長的正道,就看到一個不到十級的臺階,通向一塊空地。兩名宿衛(wèi)軍軍士腰挎橫刀,手持長矛分立在臺階入口兩邊,他們身上黑色的步軍甲襯托著周圍的環(huán)境顯得無比的凝重。他們頭戴著北府步軍標準的灰黑色圓盤倒頂頭盔,頭盔的兩根繩子從他們的耳邊穿過,系在下巴下,將頭盔牢牢地拴在了他們的頭上,正中間的矛尖盔頂下纏著一根白色布條,不長的布帶在風中緩緩地飄動著。北府軍陣遠用神臂強弩,箭如雨發(fā),中者皆傷;近有重甲長矛,突刺浪進,勢不可擋。只要他下決心拼死一戰(zhàn),我還想不出怎么樣去擋住他們。白純的話讓眾人心里不由地嘀咕起來,還有幾個將領開始交頭接耳起來。
在黃昏的時候,燕軍終于頂不住了,他們在石墻前已經變黑的山坡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尸體,黯然地撤了回來。三萬燕軍損失了兩千多人,但是依然沒有達到目的-占據狼孟亭。但是站在女墻后面地苻堅也成了城下弓箭手的靶子,只見飛舞的箭矢一支接著一支射中了苻堅,卻被北府精制地將軍連環(huán)山文甲給擋住了,但是那一個個白色的箭坑卻布滿了苻堅渾身上。有兩支箭射中了胳膊等空擋地方,滲出的鮮血流遍身體,將金色的鎧甲變成了黑紅色。
當然了,我們還有青海將軍部屬。他們早就占據控制海頭、樓蘭、善等國,算是為我北府在西域南道打下了釘子。根據以上情況,我們樞密院制定了三套作戰(zhàn)方案。剛才還占據優(yōu)勢的周軍前軍看到自己后陣一片混亂,有心人回頭一看,只見后陣全亂了,一支打著燕軍旗號的騎兵穿行其中,看上去好像是有燕軍奔襲了本軍的后陣,更重要的是本應該在中軍的那面代表苻堅的王旗居然跑到后軍,難道是大王逃跑了?
輕騎們像是在旁觀一群猴子,對著數萬聯軍一通指指點點,然后掉轉馬頭又消失在眾人的視線里。眾人不由一陣大喜,看來自己這位大將軍步步早有先機,連這種事情都會想到前面去了,對曾華的敬佩之意更是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。
聽到這里,慕容垂慢慢地把目光從慕容直的身后移了過來。在慕容直的身后,數千燕軍軍士們正三三兩兩地從前面退了下來。他們不管有沒有受傷,臉上都是極度的疲憊。他們或者互相攙扶著,或者拄著手里的長矛,緩緩地走著,除了腳步聲,就只有旁邊的烏尺水嘩嘩的聲音。他們經過時只是默默地看了一眼慕容垂,然后慢慢地走入到后面的黑『色』。你們難道沒有聽說嗎?柔然地跋提在漠南吃了大虧,十萬鐵騎被數十萬南軍打得屁滾尿流。律協(xié)沉聲說道。
萬勝!萬勝!排山倒海般的歡呼從沉寂中爆發(fā)出來。無數地長矛和鋼刀在陽光中被高高地舉起,如同那一浪卷過一浪地波濤,預示著一場席卷天地地暴風雨即將到來。曾華那蒼勁有力卻實在難看的筆跡躍然紙上,上面寫得東西和以前那些信大同小異,無非是曾華告訴范敏等人,他在西域很好,雖然只能是每天面粉搭配著羊肉吃,但是做為主帥,曾華能喝到最上乘的南山茶葉刮油,而且現在能喝上西域特產的葡萄酒,也算是一種享受。